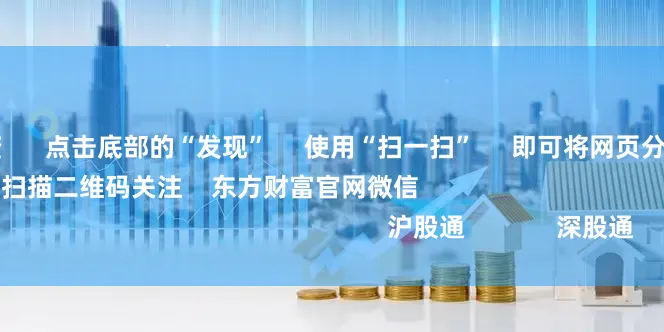每个月人们都会关注到那颗离地球越来越近的小行星,隔三岔五就有一轮新的末日预言推送到你的时间线,“三体人”开通了社交账号,被人类花式催工作进度,“你不来,有的是人来”……我们对“终结”的想象,好像早已成为定番。
是这样。从不同宗教和神话中的“大洪水”“天启”“审判日”,到21世纪初罗兰·艾默里奇那些毁天灭地的灾难片,我们一直热衷幻想世界要完——谁将杀死人类文明?瞬间的,还是缓慢的?人类能够对抗远超我们控制的灾难、逃出生天吗?主宰地球的物种消失后,留下的将是什么?
也许是出于对不可控情境的共同焦虑、对集体消亡的“公平性”怀抱期待,或者是迫近的死亡让人重新思考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,我们在不同时刻对末日的描摹,跨越了媒介、文明和代际,既是恐惧的投射,也是绑定全人类命运的集体梦境。
“1999展:不存在的那一天的记忆”,7.11-9.27,东京六本木博物馆
正在进行中的“1999展:不存在的那一天的记忆”就是这样一场末日展,它想象了诺查丹玛斯末日预言成真的时间线。当灾难如期而至,平凡度日的人们在经历什么?为什么26年后的今天,我们还无法停止想象那个时刻?
NOWNESS前往东京六本木博物馆,和策展团队B3RMUDA(读作BERMUDA three)的佐藤直子、背筋、西山将贵,共同探索连接人类的末日梦。

六本木博物馆外排起长队,草地上立着渲染恐怖气氛的红色指示牌,空气里却只有年轻人的说笑声。日本的夏天向来与鬼屋和怪谈相伴,人们习惯在炎热的季节里借助恐怖内容来获得一丝凉意。年轻的观众带着去鬼屋探险般的轻松心态,期待惊吓,也期待娱乐。
一本预言之书揭示了整个1999展的线索——诺查丹玛斯预言“恐怖之王”将在1999年从天而降,带来终结;电视正播放着有关预言的新闻,阳台外的天空逐渐变成血色……
世纪末的细节埋藏在各种精心设置的房间细节里,我们像是踏入了预言成真的另一条时间线。展览空间被有意切分:一部分场景宏伟如宗教祭坛;另一部分则在日常的氛围里暗含不安与阴影。年轻的观众很快找到了与当下的接口,现场随处可见拍照打卡的身影。末日意象被重新编码,成为一种社交化的视觉体验。


图片来自“1999展:不存在的那一天的记忆”
直到展览的尾声,两条时间线彼此重叠,1999年的世纪末预言闯入2025年的现实,观众才恍然大悟——迎接他们的并非终极景象,更像是一种错愕与反转。既不同于鬼屋式的即时惊吓,也不同于纯粹以出片为目的的装置艺术,这种由叙事进入氛围,最终回归叙事的空间营造,使人不得不思考:末日的期待,是人类共同的幻想,还是个体最隐秘的欲望?未曾到来的终结与当下社会的焦虑交织在一起,构成一则现实的寓言。

策划展览的恐怖题材创作团体B3RMUDA,其三位成员都是恐怖类型的创作者,所以为什么不做一个更直白的恐怖企划呢?
这其实是团队最早决定的方向。主策展人佐藤直子告诉我们:“在策划时我们就很明确,不想做成那种单纯传达恐惧、像鬼屋一样只是让人感到不安或害怕的展览。”

B3RMUDA的成员来自看似平行的创作世界:佐藤直子,曾担任经典恐怖游戏《SIREN》系列的剧本创作,首作于2003年上市,至今仍拥有无数拥趸 ;背筋,日本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恐怖小说家,出道作《关于近畿地方的某处》以现实怪谈为入口,出版以来即成为“爆款”,并延展为电影等多种形态;西山将贵,导演,迷恋科幻与恐怖的边界,首部长片《Invisible Half》已入围独立电影节Raindance。三人带着“一起玩”的心态,借用游戏《SIREN》中虚构的偶像团“B3RMUDA”的名字,组成了跨越媒介的恐怖题材创作团体。



他们的首次公开行动并非在各自熟悉的领域,而是一场线下展览。这意料之外的选择,一开始便为展览带来了独特的关注度与讨论空间。
佐藤说:“我们不想用‘世界末日’这个主题去制作刻意夸张、渲染黑暗的东西,而是想以它为主轴,让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”正因为如此,“我们尤其希望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能来看看。”

作家背筋负责展览的故事营造。他说,一提到1999,大家自然会想到“1999年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”。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和绝望,追根溯源,其实源于对社会的不安,“反正继续活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事,不如大家一起毁灭吧”。
“展览最后时间线交汇的设置,其实一种有意的混合与交错。这种追求毁灭的情绪其实是跨越世代存在的。现在的人是否对生活充满希望呢?事实并非如此。
“日本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文学类型‘轻小说’,这个领域中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,就是‘异世界转生’。这些创作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。这个世代从出生开始,日本的经济状况就一直很糟糕,在他们成长的整个过程中,几乎从未有过真正的好转。


“因此,这一代人的价值观里,往往包含着对未来某种程度的放弃。这种心态不仅存在于创作者身上,也同样存在于读者身上。与其让现实变好,他们更倾向于‘想重新投胎’‘想去另一个世界’。大家都清楚,这种事不可能发生,但至少在创作和想象力的世界里,人们仍然带着那种希望。”

最年轻的西山出生于1999年6月,恰好是预言中世界末日的前一个月。在他的记忆中,2012年的玛雅历末日预言带来的冲击更让人难忘:
“当时我还在读小学二、三年级,就在网上看到有关玛雅大预言的文章,说世界会在2012年毁灭。我住在爱媛县非常偏远的农村,村里没人讨论这事,那感觉就像只有我一个人,通过互联网知道了这件大事。等到2011年的某天,我居然在电视的早间新闻里看到了关于玛雅预言的报道,甚至爱媛当地的报纸也开始刊登对玛雅预言的各种看法。

“那一刻我心想:咦?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吗?怎么全社会都开始害怕了?该不会真的要发生了吧?我对预言信以为真。世界会结束的恐惧在那段时间几乎天天伴随着我。”
逃过末日预言,他对人类末日的想象却颇为浪漫:“我觉得人类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能忍受孤独的生物。随着人类不断向宇宙扩展,最终会逐渐分散到各个星球,不再执着于某一个故乡。
“现实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倾向,比如明明在日本出生长大,却有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海外生活。人类会被自己的探索驱动,向宇宙各地扩散,在这个过程中,种族会逐渐稀薄,越来越分散,经过成千上万年,有一天某个人类在某个星球上死去,却没有意识到——自己就是最后一个人类。人类的自我中心与孤独耐性,会悄然地终结整个人类文明。我希望有一天能把它拍成电影。”


与之相对的,背筋对终结的想象则十分理性:“我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人,在人类可以想象的范围内,导致灭亡的原因大概两个。一是全球规模的流行疾病,另一个就是气候变化或者地壳变动带来的自然灾害。
“不过说到人类的终结,我们往往会倾向于用浪漫化的方式去想象。比如像亚当和夏娃那样,最后只剩下一男一女,他们手牵着手走向死亡之类的场景。借用西山所说的:在某个曾是无菌室的地方,或是地下设施里,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,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最后的幸存者,最终就这样悄然死去。原因大概会是疾病,或者自然灾害。大概就是如此不浪漫的结尾。”
这份理性的来源,也许和他的家庭有关:“我的父亲是僧侣。从小我就会听到很多关于死后的事,为了死后会去到怎样的地方而在现世积累善行之类的。在这种影响下,我渐渐觉得,所谓的终末,其实就是自己与世界的连接被切断的那一刻。当我死去的那一刻,就是世界的终结。”

佐藤的末日想象则来自于亲身经历:“全身麻醉时我曾经历过幻觉,自己的身体仿佛一点点碎裂消失,紧接着,一种巨大的多幸感笼罩了全身,我突然意识到,原来如此!一切都是弥散在世界里的粒子,只是恰好在刚才以‘我’的形态聚合在一起而已。那是种非常宗教性的体验。
“从那之后我觉得,所谓的开始和结束,其实都是意识的产物。如果游戏规则改变,也许我们会突然发现,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存在,只是恰好到刚才为止,它以一种‘存在’的样貌呈现过而已。
“说到世界的终结会从何开始,我认为那将是在人类失去想象力之时。因为有了构建和维持世界所必须的想象力,我们才会思考:为什么不能杀人,为什么不能伤害他人。怜悯他人、不去伤害他人,这一切都建立在想象力之上。失去想象力的那一刻,人类便会开始互相残杀,战争也会随之爆发。”

展览并不仅仅关于末日本身,并不意外地,它还唤起了另一层意象:再生。
在日本的创作传统里,“末日”从来不是孤立的终结,而往往与“再生”相伴相生,究其原因,也许是隐藏在自然灾害里的无常感。

佐藤告诉我们:“东日本大地震时,我看过被海啸改变的海岸,那种景象让人无比悲伤,但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——自己只能置身于这巨大的变化中。这是自然和历史长河里早已存在的力量。有了这种体验,‘无常’已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概念,而是深深刻进生活、文化与情感中的现实。
“在欧洲,很多建筑是石头造的,可以保存成百上千年,留下历史的痕迹。但在日本,建筑多是木质,会不断损坏,消失,再重建。灾厄与救赎,就像是硬币的两面。”


“把坏掉的东西修好,也是日本的一种集体美学。”这是西山的感受:“也许这不是日本人特有的观念,但与其把坏掉的东西换成新的、升级成更好的,我们会先想着去把它恢复原状。
“在日本,人们常常会觉得熟悉的物品、或是有感情依恋的地方,都会有神灵寄宿在其中。这是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。这种对事物与地方的珍视,也是日本人集体意识的根基。即便展览描绘的是世界终结、个体走到尽头的情境,也仍然会探讨:我们是不是依然渴望回到原本的样子?”
在面对毁灭的同时,总会渴望新的开端;而再生的征兆,也总是在无常的阴影下显得格外珍贵。也许展览正是通过这种双重性,让“再生”成为一种复杂的体验,而非单纯的安慰。

B3RMUDA的末日推荐
西山将贵:Karen Thompson Walker的小说《奇迹的时代》(The Age of Miracles)。
我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本小说,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加州女孩。某天,她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地球的自转正在逐渐减慢,这种现象被称为“the slowing”。这意味着地球会一点点慢下来,世界会在十年、二十年间走向灭亡。
可即便如此,人类还是要在这十年、二十年里继续生活。小说讲的就是世界的缓慢终结与女孩的日常生活交错、摇摆的过程。
这本书里描写的世界的终焉对我来说既浪漫又深邃,更重要的是,这本书让我思考:当地球最终寂静下来,人类究竟能留下什么?或者说,是否还有“留下”的价值?这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。

《奇迹的时代》
背筋:电影《瞬息全宇宙》
在为展览撰写故事时,我脑海里一直萦绕着这部作品。一个陷入困境的主妇,在另一个世界里却是超级英雄,或是一块石头。它并不是单纯把主角投射成理想化的模样,而是非常认真地在探讨平行世界的概念,走向完全不可预测,始终让人紧张、兴奋。
那种感觉,我觉得和这次展览里所说的“再生”这个部分很接近。它既代表希望,也包含着无常感,让我感受到了共振。


瞬息全宇宙(2022)
佐藤直子:萩尾望都的SF漫画《银之三角》《百亿日千亿夜》
这两部作品对我意义特别重大。只要一想到“世界的外侧”或者“超越时间的存在”,脑海里必然会浮现这两部作品,喜欢到会把其中自己最爱的场景截图保存,随时都能拿出来看看。
《百亿日千亿夜》里安排了让世界不断走向毁灭的存在,而主角阿修罗王则不停地向“世界的外侧”前进,但最终仍无法与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对峙,反复落入新的战斗。它让我知道,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“不要放弃”。

《百亿日千亿夜》



NOWNESS秋季刊和你一样沉迷无用之物。盲盒为什么令人上瘾?委托一场约会能好过真实的恋爱?碎片化的视频如何抚慰了我们?为什么电影人不知疲倦地奔赴电影节?沉迷是逃避现实的方式,还是在把我们推进更深的虚无?疯狂与热爱,往往只有一线之隔。当你沉迷时,沉迷也在凝视你。




实盘配资最狠的三个平台,炒股配资开平台,十大股票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深圳配资开户《本草纲目》说它“助气壮筋骨”
- 下一篇:没有了